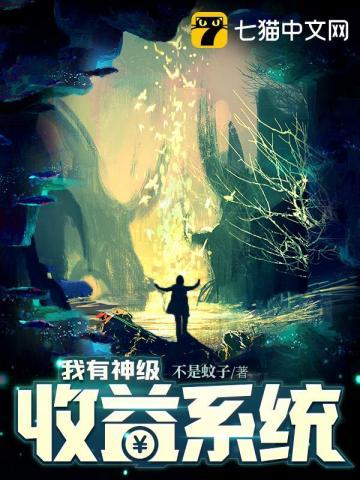久久小说网>权臣他为何那样 > 5060(第25页)
5060(第25页)
“你睡不着什么,贪污的是冯际良又不是你。”林禄铎不以为然地喝了口茶,“你又没有与他同流合污,老夫也没有与他同流合污。我们都清清白白,有何救命之处?”
“是……是……但是……”韦颂塘紧张地搓着手,“但是现有拓跋绥后有瑞王,现在又有冯大人……臣实在难以不将这些人与一件事牵连。”
林禄铎明知故问:“什么事?”
“怀霜案。”
林禄铎将杯子一搁,嗒地一声,他脸上仍旧没有什么表情:“这话可不能乱说。”
“大人,都到此时了,臣不妨直言!虽然冯际良的贪污案没有和赵平川的死联系起来,但定远军即将入京,万一说出了什么,下一个要死的人就一定是我!”
当年三法司会审赵氏谋逆案,时任御史大夫的林禄铎、大理寺卿的耿仕宜皆以将赵氏踩到底为目标,唯一能够说句公道话的本应只有韦颂塘。
可惜,他是个贰臣墙头草,赵氏风光时趋之若鹜,赵氏跌落尘埃时他也要踩上一脚,他看出赵氏大势已去,遂了林禄铎与耿仕宜的愿,对秦云绮施以重刑,强迫画押,这才定了赵氏的罪。
如果真是为了怀霜案,那首当其冲要死的人,可不就是他吗?
韦颂塘怕极了,林禄铎听罢却幽幽道:“怕什么,你不是还有靳相月这个好儿媳吗?”
韦颂塘一怔,林禄铎波澜不惊地瞧着他眼中的慌乱一点一点褪去,如激荡的浪花慢慢平息,终于恢复了平静。
是啊,他还有靳相月。
靳相月这个人本身不重要,但她的身份很重要。
她是孝成皇后唯一的女儿,也是靳怀霜唯一的亲妹妹,现在,她还是韦家的儿媳妇。
哪怕怀霜案相关之人真的被牵扯调查,靳相月看在韦正安的面上,也理应出言,保自己一命。
“懿宁公主不是个善茬,却也不是个傻子,她都嫁到你们家了,若是传出你与怀霜案有关,她岂不是嫁给了仇人。”林禄铎终于将他扶起来,“为了她自己,她怎么会呢。”
韦颂塘急促的呼吸缓缓平复,林禄铎给了他最后一颗定心丸。
“前几个人都死了,我们再不能自乱阵脚,一定要团结一心,有事你再秘密送信给我,如此慌张,反倒容易被察觉到什么。”
“是,是!”韦颂塘长揖一礼,“臣多谢丞相大人指点迷津。”
林禄铎把人客客气气地请出了门,待韦颂塘前脚刚走,后脚林禄铎脸色一沉。
脚步声徐徐踏来,靳怀霁在他身后站定:“韦颂塘这棵墙头草,但嗅觉却还是很敏锐。”
“怀霜案三罪,如今就剩下一件‘密谋逼宫’,他虽胆怯,但说的未必不是隐患。”林禄铎抬头看着暗沉的天幕,“山雨欲来,殿下也还请做好准备。”
靳怀霁冷笑一声:“真没想到,都七八年了,居然还能有靳怀霜一党意图平反,谁说我们废太子只懂死读圣贤书的,我看这权谋心术他也不是不会。”
“无论如何,殿下前星已定,大权在握,靳怀霜、靳怀霄已死,剩下一个靳怀霖不成气候,殿下只需走好最后一步,老臣定会扶着殿下,一步步走上金銮殿。”
林禄铎杀意浓重:“至于旁的,替死鬼这不是有现成的吗?”
“沙沙”。
林禄铎和靳怀霁同时转头:“谁?”
树影动了动,一身穿鹅黄色裙裾的女人缓缓走出,手上还托着一只茶盘。
二人神色一松,靳怀霁迎上去,替她接过手中东西,语气是从未对旁人有过的温柔和煦:“鹤笙,夜寒露重,你怎么出来了?”
林鹤笙柔柔地摇了摇头:“看你们站在外面聊天,怕你们冷,我就送暖茶来。”
她顿了顿:“刚刚你们……在聊什么呢?”
*
接到纪凛他们回京消息,秦黯他们早早就在城外候着了。
几人偷偷见了一面,纪凛揽着赵敬时下车,甫一看到赵敬时那苍白憔悴的脸色,秦黯的眼尾霎时红了。
却偏要嘴硬:“你不是天下第一吗?怎么还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。”
赵敬时摇了摇头,无奈道:“一时不慎,不过,我给你带了个东西。”
纪凛自马车上摸出一把利刃,上面的刀柄处犹有血迹,秦黯接过,指腹自那抹鲜红抚过。
“这是……”
“敛晴姐的斩。马。刀。”
秦黯霎时变了脸色,赵敬时叹了口气,轻声道:“我只找到了这个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