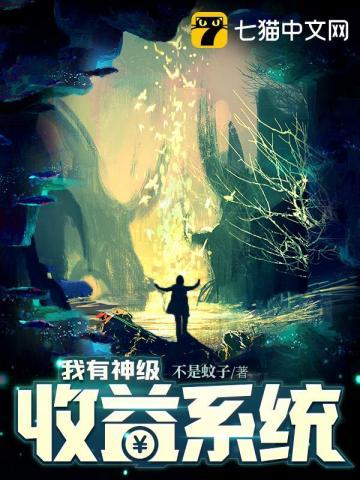久久小说网>权臣他为何那样 > 5060(第24页)
5060(第24页)
“醒了?”
赵敬时高烧已退,身体亏空得厉害,因此醒来时还分不清今夕何夕,睁眼见自己躺在纪凛怀里,张口便道:“外祖已经来了?”
纪凛抱着人的手一僵,赵敬时缓了下神,才意识到刚才自己说了什么。
他揪着纪凛领口的手紧了紧又松开:“抱歉,我睡迷糊了。”
“无碍,我倒多希望是我睡迷糊了。”纪凛察觉到他要下去的微弱挣扎,用了下力把人搂紧了,“我宁可这所谓权臣不过是一场虚妄梦,梦醒我们还在延宁宫。”
赵敬时垂下眼,不知在想些什么,半晌,才长叹一句:“梦里不知身是客罢了。”
纪凛听不得他说这个,只好转开话题,伸手覆上他颈侧疤痕:“阙州事暂且告一段落,你现在可以告诉我,这是怎么来的了吗?”
赵敬时下意识抿了抿唇。
这就是不愿意的意思了,纪凛熟悉他的所有小动作,赵敬时眼珠微微一转,就是编谎话的开始。
但他当然不想听谎话:“莫诓我,阿时。”
赵敬时刚想张开嘴就又闭上了。
“我还没想好要如何同你讲,讲我当年的事情。”纪凛的目光太灼热,赵敬时别开脸,“我从没想过要和你相认。”
“我知道,你想报仇雪恨后,这副躯壳就没了存在的意义和停留的价值,没了恨意,在你心中你自己只是一具行尸走肉,所以你要无牵无挂地走。”
赵敬时不语,算是默认。
纪凛咽下喉头酸涩:“可是现在,事有急变,你我相认,又要如何做到无牵无挂?”
赵敬时眼睫一抖,缓缓抬眼:“也可以。”
“你不要再说你与你不是一个人这种话,你明知道的,不过是掩耳盗铃、自欺欺人。”
赵敬时喟叹道:“但是纪凛,我真的没有办法,再去爱一个人了。”
他语速不快,说多了还会轻咳,但不影响这些话是他深思熟虑后的结果:“靳怀霜能够爱人,因为他有足够的爱。可赵敬时没有,我只有悔愧、内疚以及恨意。而你,纪凛,没有我你会活得更好的。”
这话让纪凛怒火中烧,但看着赵敬时苍白的脸色,又硬生生按捺下去,憋得嗓子都哑了。
“你凭何觉得我会活得更好?”
赵敬时移开目光:“这世上任何一个人没了我,都会更好。”
纪凛看着他倔强的侧脸,只能缓缓抱紧了他温热的身躯。
他知道有些事情急不得,赵敬时心魔太重、愧疚也太深,对自己的唾弃更不是一朝一夕形成——七年的颠沛流离、生死一线,才塑造了眼前的这个赵敬时。
在剩下四个人死之前,赵敬时不会走,他就还有时间。
赵敬时动了动:“有点闷,开窗透透气吧,到哪里了?”
“马上进京城了。”
纪凛伸出一条手臂,将窗户推了一条缝,京城的四五月已是和煦的夏,处处树枝葳蕤,郁郁葱葱。
“今夜,怕是有好些人要睡不着觉了。”
*
韦颂塘自冯际良处决那天就没睡好觉了。
身为刑部尚书,除非皇帝特派,监刑一直是他的责任,那天冯际良背着斩首的罪名跪在台中央,没有慌乱没有悔恨,只是冷冷地望着他。
似乎在告诉他,等着吧,我的今日就是你的明日。
韦颂塘终于按捺不住,趁着夜黑风高赶往了林府。
今日太子妃回家探亲,他求了好几遍让林府家丁代为通传,才终于得到放行的消息。
林鹤笙先回了出嫁前的闺房,林禄铎坐在正厅里,杯中茶还未下一半,看起来被韦颂塘打搅了与女儿说话很不开心。
但此刻韦颂塘也顾不得那么多了,林禄铎瞥了他一眼,抬了抬手示意小厮都退下。
等到屋里只有他两人时,韦颂塘双膝一弯,扑通地跪了下来。
“干什么?干什么?”林禄铎觑了他一眼,却也没有要扶人的意思,“成何体统?”
“求大人救我!!”韦颂塘鼻头一酸,倏然落泪,“臣自冯大人死后一直心慌得很,夜夜不得安枕,求丞相大人指点迷津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