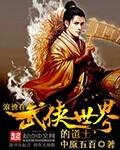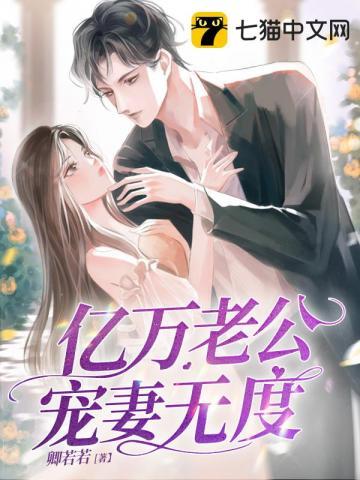久久小说网>全球尸变,但我回村种田 > 6070(第17页)
6070(第17页)
“除了你妈妈外,我其实还有过两个孩子,一个还在肚子里的时候,你姥爷有一天晚上喝醉了回来,因为我月份大了,没有及时起床给他开门,而对我拳打脚踢流掉了。”
“另一个,是你姥爷心心念念盼望着的儿子,但很不幸的是,在他一岁多刚开始蹒跚学步的时候,跟着你姥爷下地,他喝多了倒在田里就睡着了,等他醒过来,孩子已经不见了。”
“我和村里的婶子们四处找,直到天黑,才打着手电筒,在距离田地几百米的旱厕里,发现了他已经泡的肿胀面目全非的尸体。”
“好在,你妈妈还是活了下来,生下你妈妈那年,我也才二十岁出头,我不懂怎么做母亲,但当看见那个男人因为你妈妈生下来是个女孩,就要把她扔到茅坑里去时,我第一次反抗了他,拿起锄头砍伤了他的脸。”
“那一刻我的心里竟是无比轻松,我很庆幸我在那一刻做了那样的选择,就如同二十年后,你妈妈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。”
“仔细想来,你妈妈在我膝下长大的时间还没有你跟着我的日子长,她就如同是另一个我一样,小小的就出去打工赚钱,到了有利用价值的时候,就被你姥爷卖到了另一座大山里,换回了咱们家里的那台大彩电。”
“当她死后,我看着你这张稚嫩却几乎和她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脸时,实在割舍不下,我知道,要是把你留在那家的话,你恐怕也会遭遇和我,和你妈妈一样的悲剧,所以我想要留下你,却遭到了你姥爷的强烈反对。”
“那是我第二次反抗他,我拿着菜刀准备和他拼命,他也许是想起了我上次拿锄头砍伤了他的脸的事,于是便默许你留了下来。”
在姜五妮的记忆里,这是她第二次反抗来自父权夫权的威压,但在姜早的记忆里却不是这样的,光是这样的时刻就有无数次。
在她到了该上学的年纪时,家里却交不起书本学杂费,她名义上的姥爷只会啪嗒啪嗒抽着旱烟,说女孩子家家的念什么书,反正也念不进去,不如让她跟着姜五妮一起做活算了,到了十来岁就寻个好人家嫁出去得了。
那一天的姜五妮大发雷霆,连吃饭的桌子都掀了,姜早从没见过她发过那么大的火,指着姥爷的鼻子就骂:“你祸害了我的一辈子,妮儿的一辈子还不够,就连枣儿也不放过吗?!有我在这个家里的一天,谁也别想打她的主意!我就算是砸锅卖铁都要供她读书!”
那后来,姜五妮卖了家里干活犁地的老牛,又在无数个夜里点着灯纳鞋垫把眼睛都熬红了,这才牵着她的手把她送进了学校里。
她总是会蹲下身,替她整理好红领巾。
“枣儿,你一定要好好念书,将来做个有出息的人,不要像我和你妈妈一样,听见了没有?”
姜早一年比一年长的高,就像迎风抽条的树枝一样,慢慢已比她还高了。
姜五妮的背影却逐渐佝偻,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辛苦劳作让她患上了腰椎病,下蹲弯腰变成了一件困难的事。
家里的鸡鸭鹅她总是在春天就早早买回来,到了次年春天就变成了她兜里沉甸甸的学费。
姜五妮也曾无数次驻足村口的小路上,等待着她放学,或者送她去远行,可是那时的姜早,满心满眼竟然都是想要早日走出大山。
跳出这个苦难的轮回,再也不要回来。
她竟没有、没有一次回头看过。
直到现在,当她幡然醒悟想要回头的时候,却发现,回首万里,故人长绝。[1]
信纸里的人仍在写着。
信外的人却早已泣不成声。
“就这样,我为你取名姜枣,希望你像咱家门前的枣子树一样,耐寒,耐旱,结出的果子却极甜,到了我去县城里为你上户口的那天,派出所窗口接待我的是一位女警员。”
“我一直深深记得她。”
“她看了看我递过来的,请村里的教书先生写的纸条,笑着又给我写下了一个字。”
“女孩子还是叫姜早吧,早就是朝阳,一天中太阳刚升起的时候,希望她以后都能像今天的阳光一样灿烂,朝气蓬勃地茁壮成长。”
“我听不懂她说的是什么意思,但我也觉得这个字很好,于是便点了点头,就这样,早就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字,但我后来还是习惯了唤你的小名,枣儿。”
“我跟你说了这么多,其实只是想让你原谅我,原谅我在生活日复一日的磋磨里也变得脾气差、暴躁、不讲理、阴阳怪气,原谅我不懂如何和孩子相处,在你小时候对你并不够好,让你吃了那么多苦,导致你成年后抗拒回家。”
姜早想起离家求学外出工作时的每一年除夕前,总会接到姜五妮打来的电话。
“枣儿,今年回家过年吗?”
电话那头的她,是那么期期艾艾地问着,却无一例外地得到了否定的回答。
她从没有,从没有在除夕这天回家和她一起团圆过,从没有,从来都没有。
“当末世来临时,我其实还有一丝庆幸,我终于可以见到我的枣儿了,终于可以和她一起过个团圆年了,这个家里有你,有小昭,还有小弥和可乐,这几年尽管生活条件艰苦,但却是我这一辈子最幸福快乐的时光。”
“你和小昭、小弥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支持和力量,如果不是你们我坚持不到现在,那次消灭村里的丧尸,你说我们是一个团队,少了谁都不行的时候,其实我心里好高兴。”
“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被人这样肯定,原来被人肯定和信赖的感觉是这样好。”
“枣儿,尽管生活里诸多苦难,但我从不后悔把你带回家,能当你的姥姥,我很高兴。”
“不知道下辈子还能不能遇见你,但你永远是我最爱的人和最值得骄傲的孩子。”
微微泛黄的纸页上,也留下了几滴已经干涸的泪渍,姜早颤抖着,从喉咙里发出了呜咽。
姜五妮继续写道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