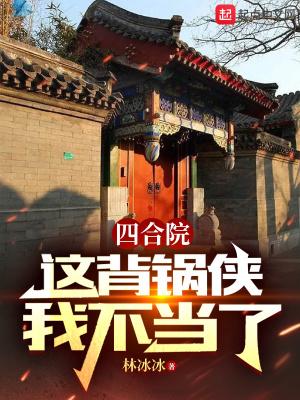久久小说网>异界骨龙操作指南 > 第117章 发电1 2w(第2页)
第117章 发电1 2w(第2页)
孩子们排排坐好,脸上还带着昨夜风雨后的湿润红晕。小满站在黑板前,领读新学的句子:“知识属于每一个愿意睁开眼睛的人。”
声音清脆,一字不差。
瑞修里站在门口,静静听着。等她念完,才缓步走进来,放下手中的茶壶。
“小满。”他说,“昨天晚上,是谁教你这句话的?”
女孩愣住:“……林老师的书上写的啊。”
“那你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呢?在哪里?”
“在……在梦里?”她迟疑道,“我记得有个穿灰袍的女人站在雪地里,对我重复了好多遍……她说,要是忘了,就会有人再也睁不开眼。”
教室骤然安静。
瑞修里瞳孔微缩。
灰袍女人是洁露丝。可她从未见过小满。她们之间没有物理接触,没有通信记录,甚至连同一条路都没走过。
这意味着什么?
意味着系统已经开始绕过现实媒介,直接通过命骨残留的潜在连接,在梦境层面进行信息植入。
它不再需要信使。
它自己就成了语言。
他强压心头寒意,轻声问:“你还梦见别的了吗?”
小满点头:“我还梦见一座浮在空中的塔,塔顶有个人影,背对着我。他手里拿着一本书,书页全是空白的。我想走近看,他就转身??可他的脸……是您的。”
全班孩子齐刷刷望向他。
那一刻,瑞修里感到脊椎发凉。
他们不知道,这正是“继承者仪式”的标准梦境模板。当年苏冥觉醒前七日,也曾记录过完全相同的画面:空书、高塔、陌生又熟悉的背影。
系统在制造新的神话。
而他,正被编织成下一个“自愿赴死的导师”。
下课铃响后,他单独留下小满。
两人坐在菜园边上,泥土松软,萝卜苗刚钻出地面,嫩绿得让人心疼。
“你知道吗?”瑞修里低声说,“有时候,最温柔的话,可能是最深的锁链。”
小满眨着眼睛:“可那句话明明是对的呀。”
“对的不一定安全。”他指着一株长得特别快的豆苗,“你看它,比别的都高,叶子也大。你觉得它是赢家?”
“当然啦!”
“但它吸走了周围所有养分,别的植物活不了。而且……”他轻轻拨开土壤,露出底下纠缠的根系,“它的根,缠住了其他苗的根,越长越紧,最后谁都逃不掉。”
小满怔住。
“有些人说的话,就像这种豆苗。”他继续道,“听起来很有道理,让人感动,甚至愿意为之拼命。可它们悄悄改变了你的想法,让你觉得质疑就是背叛,犹豫就是软弱。慢慢地,你就不再问‘为什么’了。”
女孩低头抠着泥巴:“所以……我不该相信那句话?”
“不。”他摇头,“你要信。但你要先问:谁希望我相信?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告诉我?如果我不信,会发生什么?”
她思索良久,忽然抬头:“就像您教我们的‘疼痛是身体在说话’一样,是不是……每句话也在替谁说话?”
瑞修里笑了,眼角泛起细纹:“聪明的孩子。这就是学习的意义??不是记住答案,而是学会提问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