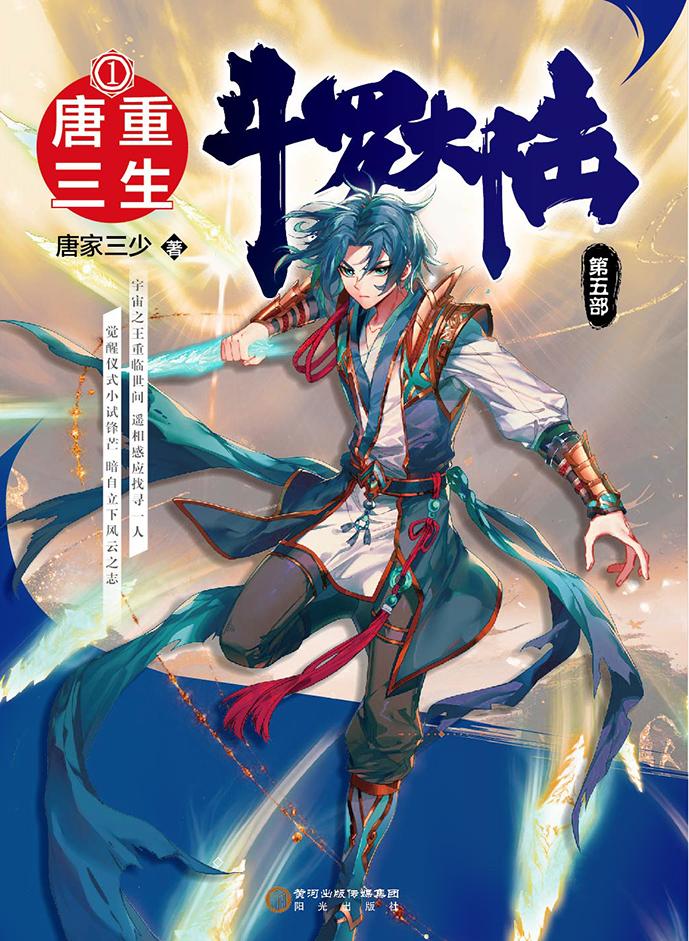久久小说网>权臣他为何那样 > 8087(第19页)
8087(第19页)
“一样什么一样!”江璧晗终于喘上了那口气,厉声打断道,“纪凛,赵敬时走了。”
在纪凛波澜不惊的目光中,江璧晗给这句有所歧义的话补充完整:“不是死了,是走了。他没有死,也不去死了。”
“他留下了。”
“砰”,包袱重重坠地,那一刻纪凛什么也听不到,也什么都想不起来了,等到他回过神来时,早已飞身跑出好远,惹得江璧晗险些没有追上他。
“但是——”江璧晗用力扯住他的衣袖,“但是,你还要给他一些时间,让他再想一想,冷静冷静。”
纪凛的心脏猛烈跳动:“他去了哪里?”
“江州,亦或是别的地方。这山川万里辽阔,去看一看没什么不好。”江璧晗平复了呼吸,想起告别时赵敬时一双眼,微微叹了口气,“作为靳怀霜,他一生受尽算计,处境悲凉;作为赵敬时,他一生只为复仇而活,从无心魂。如今他彻底剥离了过去,你总要给他些时间,让他明白,他这一生,到底是为了什么。”
纪凛眨了眨眼,才发现自己早已泪流满面。
“纪大人,你若是想去阙州蹲他,我不拦你,但有可能你蹲不到。”江璧晗将染了尘灰的包袱往他怀里一甩,“你要等他吗?”
“等。”
怎么会不等。
“哪怕要等一辈子,也等。”
*
隆和三十二年五月初二,靳明祈驾崩,享年五十二岁,谥号曰“昭”,庙号宣宗。
皇四子靳怀霖继承大统,改元建宁。因新帝年幼,由丞相纪凛辅政,太后江璧晗垂帘听政。
靳明祈留下的事情太多太杂,等到正式安排靳怀霖登基,已经到了五月末。
五月廿七日,黄道吉日,新帝登基。
仲夏天气愈发潮热,靳怀霖的登基大典忙了一上午,所有人早已汗水涔涔,纪凛身为辅政大臣,忙得连口水都没有空闲喝上一口。
好不容易挨到结束,他前脚刚回纪府,后脚就被人找上了门。
纪凛悻悻地收回还没碰到茶杯的手:“有何……”
来者是靳相月。
纪凛下意识后退一步,果不其然,懿宁长公主开口便是:“我哥哥呢!!”
“长公主殿下,稍安勿躁。”
纪凛揉了揉额角,连日的繁忙强迫他能够不去揣测赵敬时如今已经走到了何方。
或许是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,也或许是汹涌澎湃的汪洋边,但无论哪里,他都明白,在这世上的某一个角落,赵敬时还好好地活着。
他太了解赵敬时,如果留下那便是真的留下,不会再寻死路,那么他只要足够耐心,就终有再相见的那一日。
纪凛最不缺的就是耐心。
他曾经用耐心等到了从泥潭中拉他出来的那只手,也曾经用耐心等到了祈福寺中的红绸,更曾经用耐心等到了那个人人都道已经故去、却迟迟不肯入他夜梦的魂魄。
所以他坚信,只要他耐住性子,终有能够接赵敬时回家的那一日。
但显然靳相月不信这个:“稍安勿躁?自从靳明祈崩逝,哥哥就失去了下落,我问夏渊,夏渊不告诉我,我问淑母妃,淑母妃也不说话,现在还有你,你们怎么都不着急呢?!”
靳相月眼珠一转,声音骤然尖锐:“纪凛,如果你敢变心,我就……”
“殿下。”纪凛无奈地压了压手掌,“纪某此生唯有你兄长一人,这一点你放心。”
“那你怎么不去找?失了下落你不着急吗?!”
“不着急。”纪凛终于可以拿起茶杯喝了一口,“因为我自始至终都相信他,也会给予他足够的自由,让他能够在被折断翅膀后一次次地生出属于自己的羽翼,再度展翅翱翔。”
“兰儿。”他学赵敬时那般唤她,如靳怀霜那般哄她,“你要相信,你哥哥从来都不是需要被保护的金丝雀,他是翱翔的鹰,是雄鹰,就该在蓝天下自由自在地飞翔。”
“而我,会是他永远的窠臼。”